艾青和他的詩(代序)
以自己誠摯的心沉浸在萬人的悲歡�、憎愛與愿望當(dāng)中。他們(這時代的詩人們)的創(chuàng)作意欲是伸展在人類的向著明日發(fā)出的愿望面前的��。唯有最不拂逆這人類的共同意志的詩人����,才會被今日的人類所崇敬,被明日的人類所追懷��。(艾青《詩與時代》)
世界上也許只有中國有新詩這個平凡而又偉大的名稱�。新詩(最初叫作白話詩)它能在有悠久的詩歌傳統(tǒng)(既完備又衰老)的中國出現(xiàn),無疑的是一個真正新奇的事物���。說它新是名副其實(shí)����,這不僅表現(xiàn)在一目了然的形式的變異上,還更為深刻地表現(xiàn)在它對于陳舊而停滯的民族文化傳統(tǒng)的沖擊和突破上面�。
七十多年來,新詩的革新精神和所取得的成就���,已為歷史所認(rèn)可�����,并成為不可逆轉(zhuǎn)的中國詩歌發(fā)展的必然的道路�。然而��,盡管新詩以異軍突起的勝利姿態(tài)切入了中國古老的壁壘森嚴(yán)的文化領(lǐng)域�����,它的成長卻并不平順�。從出現(xiàn)到現(xiàn)在�,經(jīng)歷了十分艱難曲折的發(fā)展過程。除去新詩自身的發(fā)育不健全�,不可避免地引起各種思想分歧和學(xué)術(shù)性論爭之外����,還不斷受到生存環(huán)境的干擾和制約��,再加上民族的危難和長期的戰(zhàn)爭�����,使新詩一直不能循著正常的軌道前進(jìn)�����。但是新詩并沒有因自身的羸弱和外部的磨難而夭折�����,它仍在困難地����、頑強(qiáng)地成長著。
值得憂慮的是�����,中國的新詩�,經(jīng)由那些勇敢而智慧的先行者的開創(chuàng)����,沖破了舊詩的禁錮之后����,卻漸漸地又出現(xiàn)了自身的危機(jī):衰頹和異化,被非詩的社會性因素所侵?jǐn)_�,常常偏離了詩歌自身發(fā)展的軌道,因而面臨著不斷危及命運(yùn)的挑戰(zhàn)����。
回顧和清理中國新詩發(fā)展歷史的經(jīng)驗(yàn)教訓(xùn)和缺陷,以及詩歌自身的問題����,是一項迫切和亟待研討的重要課題。歷史在艱難地前進(jìn)��,中國詩歌也必須不斷地在藝術(shù)上求得嬗變和革新��,否則�,新詩也可能變成舊詩���。幾十年來�����,已經(jīng)有許多盛極一時的詩變得陳舊不堪���,廣大讀者對于它們的衰敗比過去對舊詩的厭棄還要強(qiáng)烈�����。
也許是無法回避的命運(yùn)����,也許是一種藝術(shù)規(guī)律��,中國的新詩����,與其他文體一樣,是在重重危難之中顯示出了它的強(qiáng)旺的生命力并逐漸變得聰敏�、堅強(qiáng)和成熟起來的。這種令人鼓舞的走向成熟的變化���,目前仍在深刻而痛楚地進(jìn)行著����。
......
艾青(19101996),原名蔣正涵���,字養(yǎng)源���,號海澄。浙江金華人�。1928年考入國立西湖藝術(shù)院。1929年�����,赴法國勤工儉學(xué)�����,主修繪畫��。1932年回國即在上海加入中國左翼美術(shù)家聯(lián)盟�,但不久后入獄,在獄中寫下《大堰河我的保姆》����。抗戰(zhàn)爆發(fā)后����,輾轉(zhuǎn)于漢口、重慶等地投入抗日救亡運(yùn)動����,1941年赴延安,任《詩刊》主編��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�����,擔(dān)任《人民文學(xué)》副主編���、全國文聯(lián)委員等職�。主要作品有詩集《大堰河》《北方》《黎明的通知》《歸來的歌》��,散文集《綠洲筆記》等����,理論著作《詩論》等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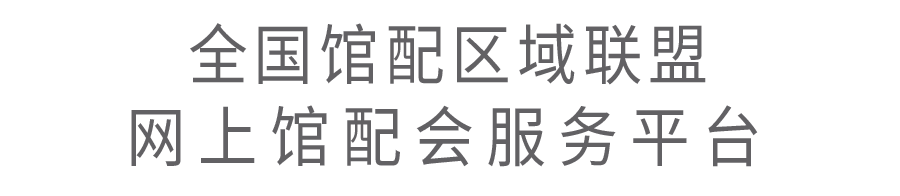
 書單推薦
書單推薦 新書推薦
新書推薦